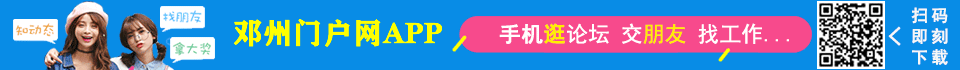百度的不错哦
字数挺多,仔细看下来,深有感触。才发现我们熟悉的大邓州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去深挖,去发现,去普及
我也来看看 我竟然看完了 感慨良多
写的真不错,我大邓州的文学家
转头回望一下邓州,追念一下邓州,我的愿望就已满足矣!
大家之作啊
写哩真好
之五 畜禽(2)
早在四千多年前,鸡便已被驯化,走进了人类的家庭。因此,同牛一样,鸡陪着我们的先祖,历经风雨,历经沧桑,从远古一直走到今天。
喔喔喔——,黎明前的晨曦里,一只雄鸡一跃跳上墙头,拍拍双翅,然后迎着鲜艳耀目的万丈光柱铺撒的朝阳,骄傲的挺起胸脯,昂扬脖颈,发出一声响亮而悠长的鸣啼;咯嗒咯嗒——,这是那只芦花鸡的叫声,它刚刚繁下了一颗椭圆形的尚带着丝丝血迹的鸡蛋,便迫不及待的飞跑到主人面前报喜,渴望着能够讨到一把谷糠;……
这样的情境,是不是隔三差五,总在你的梦里闪现?
是的。这又怎能轻易的忘怀呢?在经济极其拮据的年代,在邓州农村,哪家的学生不是依靠着卖鸡卖蛋的钱来缴纳学费杂费,来换回铅笔作业本呢?而哪家的饭碗、灯盏不是依靠着卖鸡卖蛋的钱来换回油盐酱醋,来换回柴油煤油呢?
如果你走出了农村,走出了邓州,或经商,或从政,在不同的道路上走向着自己的人生辉煌,当你面对着鲜花、掌声和无处不在的钦羡仰慕的目光时,回首往事,回望故土,你是不是应该特别感念我们的母亲曾经饲喂过的、为你默默的做出过贡献的那只鸡,那群鸡?……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在邓州农村有句非常流行的话,叫“从鸡屁股里掏钱”。这话虽然听起来粗俗,但却绝对是事实。
开春了,天暖了,该是母鸡们“捞窝”的时候了。“捞窝”是邓州农村的通俗说法,就是成年母鸡孵育小鸡娃的意思。并不是所有的成年母鸡都会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捞窝”,一群同龄的母鸡中,一只母鸡鸡冠发红,咯儿咯儿的叫着,一看见小鸡娃便两眼发直,满脸痴痴的表情,而且尽管肚里并没有蛋,但却赖在鸡窝里不肯起身;于是,家庭主妇们就明白了:这只母鸡想要“捞窝”了。
有时候,碰巧这家的家庭主妇也感觉到是该孵育一窝小鸡娃来壮大家里的鸡群了,也碰巧学生的纸笔钱、家里的油盐钱都有了着落,不需要再“从鸡屁股里掏钱”了,——因为“捞窝”期间不能繁蛋,所以一般情况下家庭主妇们是不愿让母鸡“捞窝”的,——于是便会很慷慨的成全这只母鸡的“捞窝”愿望。
主妇们先将家里攒积的新鲜鸡蛋全部搬取出来,——大多都是放在一个口小肚圆的酱色釉坛里,——然后把门板半掩起来,蹲在门后的旮旯里左手捏着鸡蛋凑近眼前,右手放在鸡蛋上方,一个一个的“照”着,看看鸡蛋较小的一端有没有“榆钱”,就是有没有一个小小的象榆树嫩叶那么大的阴影。如果有,那就说明这只鸡蛋受过精,将来有可能孵出小鸡娃;如果没有,那就根本不可能孵出小鸡娃了。母鸡“捞窝”,正常情况下每次需要二十到三十个受过精的鸡蛋,——如果太少,费时费力,划算不着;如果太多,母鸡的翅膀包揽不下,就会出现“荒蛋”。那些家里有“榆钱”的鸡蛋不够母鸡孵育一窝的,主妇们就会拿着没有“榆钱”的鸡蛋去往别人家里换取有“榆钱”的鸡蛋。
鸡蛋受精的过程,在邓州农村俗称“公鸡踏蛋”,自然发生在公鸡和母鸡之间。一群母鸡正在土堆前一边讨论国际形势一边用脚爪抛土觅食,对面便走过来了一只公鸡。那公鸡围绕着鸡群中最俊俏的一只小母鸡转悠一周,忽然就耷下一只翅膀,口里发出咯咯的叫声;这叫声如果翻译作我们人类的话,应是:妹纸,劫个色吧!小母鸡当然不同意了,就咯咯的回应一声;这回应如果翻译作我们人类的话,可能是:讨厌,这光天化日滴,而且又当着这么多姐妹滴面, ——啊呀,你让银家好好害羞耶!但也可能是:劫你妹啊,没看见老娘正在忙着抛食吃吗?
——说声劫色就劫色,你以为老娘是“鸡”啊!回应完毕转头就跑。公鸡一言既出当然驷马难追,便在后面紧紧的狂追不舍;终于将小母鸡逼到了墙角里面,长喙叼着小母鸡的冠翎,双脚一跃就踏上了小母鸡的背。七八岁的孩童们并不明白这种交配是鸡界一种传宗接代的本能,只管拍着手,咿咿呀呀的哼唱着那首在邓州流传了千年的乡村古谣:
公鸡撵母鸡,
撵到墙角里。
母鸡说:饶了吧!
公鸡说:不可以,
好不容易撵上你!
……
从鸡蛋放进鸡窝至小鸡娃出壳,需要二十一天的时间。在这二十一天里,“捞窝”的母鸡除了饮食、便溺之外,需要日夜不停的匍匐窝中,伸展双翅将所有的鸡蛋全部包揽起来,用体温温暖着它们;如果某颗鸡蛋滚至鸡窝边缘,母鸡就会小心翼翼的伸出长喙将其重新推转回来。生命的孕育是一项伟大而艰辛的历程,由于天气炎热,条件简陋,一场孵卵,往往会使母鸡毛羽脱落,精神憔悴,形体更是羸瘦得不成模样。
家有“捞窝”母鸡的主妇们总是扳着手指头一天一天的算计着时间。在第二十一天的上午,她们会端来大半盆的温水放在鸡窝旁边,然后将母鸡孵过的鸡蛋一颗一颗放进水里。放进水里后,有的鸡蛋上上下下、时沉时浮,这叫“踩水”,凡会踩水的鸡蛋都有破壳而出小鸡娃的希望;有的鸡蛋则完全沉进水底,一动不动,这样的鸡蛋或是“毛蛋”,即在孵卵过程中已发育成形的小鸡娃“胎死腹中”,如果剥开蛋壳,一个毛羽俱全的小鸡娃便会展现眼前,可惜早已死去,或是“荒蛋”,即在孵卵过程中可能母鸡没有照顾好,导致胚胎尚未开始发育便已戛然而止。“毛蛋”、“荒蛋”,均没有孵出小鸡娃的希望,统称“坏蛋”,所以在邓州农村又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歇后语:二十一天不出小鸡娃,——坏蛋!
“叽叽”,鸡蛋较小一端的蛋壳发皱了,紧接着微微破裂,现出一个小洞,这个小洞便是小鸡娃用嘴巴啄开来的;啄出小洞的小鸡娃先将嘴巴透出小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然后就一面“叽叽”叫着,一面开始使劲的挣扎,几经努力,终于挣破跳出了包裹着它的鸡蛋壳。跳出鸡蛋壳的小鸡娃回望一眼它曾经居住过的蛋壳后,就开始跟在母亲后面跑来跑去的觅食玩耍了;尽管刚刚挣脱蛋壳的时候,它们的毛羽湿漉漉的黏在身上,然而很快就会变干,或嫩黄,或黧黑,嘴巴脚趾净洁而鲜亮,毛茸茸的极显可爱娇态。如果有的鸡蛋里面的小鸡娃挣得困难,长久不能脱离蛋壳,那就说明这只小鸡娃的体力较弱,这时候便需要依靠母鸡用嘴巴来帮助啄破蛋壳了。
等到所有的小鸡娃全部破壳而出后,尽管刚刚经历过一场艰辛的劳作,形神俱疲,但“捞窝”的母鸡还是会带上小鸡娃,排作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出门外,向着其他没有“捞窝”的姐妹们夸示炫耀了。
带着小鸡娃的母鸡一来特别富有爱心,每当从沙土里刨出一粒草籽或是在草丛中捉到一条虫子的时候,它会立即咕咕的召唤着所有的宝宝们过来分吃,而到了夜里,或者遇上阴雨天气,它又会张开翅膀,让所有的宝宝们贴着它的并不宽广的胸怀躲避黑暗,躲避寒冷;二来变得特别勇敢,每当有猪、狗、猫从宝宝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它会立即张开双翅,乍起翎毛,眼珠瞪得溜圆,摆出满副破釜沉舟、不惜一战的架势,警告着这些庞然大物们不得伤害自己的宝贝孩子。
之一 水
据说,在西北某些干旱地区,由于严重缺水,人一辈子只能洗三次澡;三次分别是在出生、结婚和去世的时候。
这样的人生听来有些苍凉,有些无奈,但也有些悲壮。
邓州这片土地虽然不象江南那样水量丰沛,但也决没有缺水缺到让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的地步。在邓州,大自然用以储水的器具是河流,是渠坝,人类自己用以储水的器具则是坑塘,是水井。
在邓州境内,纵横错杂的流淌着29条河流,其中较成气候的为严、赵、刁、湍。四条河流中,赵河、严陵河俱为涓涓细流,名不见经传,几无可圈点处;湍河最具规模,最值一书,可惜我已在《湍河弯弯流邓州》一文中做过了详尽介绍,因此在这里,只能约略的谈下刁河了。
刁河上游支流多达数条,下游主流河道却狭窄得不过三丈五丈;平日里水流脉脉,看似温驯犹若处子,然则一旦突遇恶风暴雨,便即浊浪排空,破堤漫灌,不是冲毁庄稼,便是浸泡房屋,极显刁恶之性。两岸居民因深受其害,故称之为“刁”。每年汛期,刁河都是两岸居民重点的防洪抗洪对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邓州虽然地近黄河,但因湍河贯穿南北,为境内最大河流,且由汉江注入长江,故属长江流域而不属黄河流域。
邓州为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季更迭异常分明。这种气候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降水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记得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往往是在夏秋之交的午后吧,一场雷鸣电闪的暴风骤雨席卷过后,村村坑塘积水满溢,家家庄田潦水横流,大小河流更是伴着滔滔轰鸣,黄水滚滚,几与两岸平齐;其雄伟磅礴气势,常令没有见过大江大河的乡民们惊叹不已。
盛夏时节,半大不小的孩童们为溽热酷暑所逼,常于中午饭后的歇晌时间,躲过父亲母亲严厉的目光,结伙搭伴去往近村的河流、塘坝中泡澡。塘坝鱼跃鹭翔,碧水翻涌着如雪的白浪;河流溶溶脉脉,清可见底,傍岸的水草为流水冲带,伏伏仰仰,舒舒缩缩,做着千百次不屈不挠的翻卷挣扎,姿势优美宛如风中轻绸一般。孩童们脱得赤条条的,或在水中尽情的做着仰泳、蛙泳、潜泳、侧泳,或站于高高的岸畔上,脚跟靠齐,双手并拢举过头顶,在满满的蓄积力量后,突然纵身一跃,猛的扎进水底,贴着淤泥潜游数米后方肯露出头来,手中便往往擎着了一尾银亮亮的大鱼。
直到完全驱除汗泥身心愉悦后,直到村头树下传来父亲恶毒的咒骂或母亲焦急的呼唤时,孩童们这才依依不舍的浮出水面。蜡白炫目的日光下,他们踩着田间草埂排作一队,赤膊裸背,头戴柳条编帽,手提收获到的菱角、鱼虾等水府特产,一路走来一路口哨欢快,为贫苦寂寥的村落增添着无限的乡情野趣。
坑塘多在村内或者村头,它们常常是妇女洗衣淘菜、男人饮牛取水的好去处。尽管围绕坑塘同样有着种种或壮烈或幽怨,说也说不完的故事,就象周大新在《香魂塘畔香油坊》中所叙的那样,但在这里我还是想撇开它们,重点写一写水井。
在邓州农村,一般每个村落都有一到两口水井;当然,如果人口特别多的话,也会有三到四口。水井大多位于村外,即便与最近的居户也保持着三二十米的距离,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水井井台多由青色条石铺叠而成,其边沿长年累月为井绳磨擦,凹陷着一道道又粗又深的印痕;井台下面,层层青砖垒砌的圆筒型的内壁上,则时常生满了毛茸茸而又湿淋淋的绿苔。
有的水井装有辘轳,汲水时候,只需将井绳盘在辘轳上,然后用力绞动把手即可将盛满水的木桶由井底提出;有的水井未装辘轳,汲水时候,便完全凭着人力一把一把的向上拔着系了水桶的井绳了。不管装没装辘轳,所有的水井自诞生之日起,井畔必会移栽上一株两株粗大的白杨树;白杨树与水井相辅相生,相依相望,浓密如盖的枝叶可以为盛夏时节前来汲水的乡民们提供一方遮蔽烈日的绿荫。
水井的井口大小不一,并无一定的尺寸,其中大的有大碾盘那么大,小的有小碾盘那么小。在老辈人的传说中,海中有海龙王,河中有河龙王,井中自然也是有着井龙王的。井龙王平日蛰居井底,管理着井下世界的事务,享受着人们四时贡献的祭品,夜间则化作龙形冉冉升出水井,踟蹰于村落上空,默默的俯察着由它养育滋润的子孙们。孩童们由此而对水井生出了敬畏之感,走村串乡逢遇水井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匍匐近前,伸长脖颈向下一望,黑幽幽的一片银亮,宁静森凉中充满着无限的神秘和怪奇;丢一块石头下去,好半天才听到“咕咚”一响,于是转身撒腿就跑,仿佛那井龙王真的会因陡受惊扰而窜出井口,一路叫骂着追赶上来似的。
邓州的大旱往往发生在春末夏初或是夏秋之交,每隔十年八年便会逢遇一次,俗称“卡脖子旱”。大旱最为严重的时候,一连数月滴雨不见,禾稼叶干梗枯,牲畜无精打采,那些地势稍高的村落水井便汲不出水来,于是就只好去往临近的地势较低的村落“借水”了。
“借”,其实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大家共同生活在一片土地上,又共同承受着旱魃的肆虐淫威,正该互帮互助,共度难关,如今邻村有难,自己虽然并不宽裕,但难道真的连桶水之谊都没有了吗?难道真的“借”了水便必要追还吗?不,不是这样的。夏日午时,邻村的“借水”队伍就迤逦而来了,多是青壮汉子,肩上挑着扁担,扁担的两端系着木桶;在井台上汲满水后,又排作一队,在扁担吱呀吱呀的颤悠声中逶迤而去,步伐走得匀而且快。为了防止水从桶沿溢出,他们便在水面上放着一支茅葶做的浮子;中途并不停歇,需要换肩时,打头的一声吆喝,两只木桶“呼”的旋转一周,数十副扁担便同时从左肩换到了右肩,动作整齐划一,姿势娴熟优美,观之令人大开眼界。
如果一口水井汲出的水渐渐浑浊,泥腥味越来越重,那么这口水井就该淘了。淘井就是将淤塞着井底泉眼的污泥清理干净,好使地下泉水源源不断的涌流而出。在邓州农村,淘井是一项颇带技术含量的体力活,需要专人指导实施。淘井时,先由一人站于井口正中(井口已经铺盖上了木板)拉着绳子的一端,另一人则拉着绳子的另一端走动一周,一面走动一面撒着白灰,这样一个以井口为圆心、直径十余来丈的大圆就成形了;然后按照白灰标示笔直的开挖下去,每挖两到三丈,大圆便要缩小一周;——挖至井底接近泉眼的时候,大圆就只有笸箩那么大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开挖过程中井壁坍塌,发生事故。
开挖的土方量很大,而且需要全部运至地面,这时候仅靠人力已经远远不能做到了,于是便搬来水桶粗的木檩,搭起三脚架,上面装上滑轮;二十多名精壮劳力一面吆着号子,一面拉着绳索,快速的往返奔跑,通过滑轮将开挖的土方一筐一筐的由井下运出。在清理井底淤泥时,为了防止泉水突然涌出,需用棉被先将泉眼死死堵住;淤泥清理完毕后,又以泉眼为圆心,按照原始的井口大小直上直下的砌上青砖,所需的砖泥自然仍由滑轮运下。等到井壁砌好,又用大块青石拌着水泥新土将四围的空间填满夯实,这才迅速拽开棉被;地下泉水登时喷涌而出,很快便盛满了半口水井。
下井淘井是件繁难而危险的活路。当挖至井底接近泉眼时,由于空间狭窄,只能容下一人,这时候就须职业的淘井人(民间称为“井匠”,光听这名字就觉很大气。)出马了。井下气温很低,淘井人常常需要穿上棉袄棉裤,坐着由滑轮承载的箩筐下去,在狭窄得几乎不能施展手脚、黯黑得几乎不能开目视物、空气稀薄得几乎不能正常呼吸的井底,一铲一铲将湿漉漉的淤泥装进筐内运出,汗水很快就将棉袄棉裤濡得里外净湿了。有的井淘到一半时,出现了井壁坍塌的事故,那在井底的淘井人自然便无生还的可能,从此只能长眠于数十米的地下了……
关于水,关于盛水的河流、渠坝,关于盛水的坑塘、水井,在邓州人的心头上刻下了太多太多永难磨灭的印痕。相信每个三十岁、四十岁以上的邓州人,不管是依旧生活在本乡本土,还是生活在异国他地,不管是为生活所迫流落街头,还是坐拥亿万身家挥霍豪奢,然而只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闭上眼睛,脑海中就必定会萦绕起一道挥之不去的河流、渠坝,或是坑塘、水井的影子……
然而遗憾的是,近三十年来,由于气候的变异,由于工业的发展和环境的恶化,亦由于人口的膨胀和用水量的剧增,邓州一带的地下水源渐现枯竭之势。如今,走过邓州的许多村落田间,你会看到坑塘堤岸依旧,但却滴水无存,或地底龟裂,或蒿草丛生,到处都在呈现着一种令人恐怖的干涸。还有水井,随着机井、压水井乃至自来水的出现,很多水井已经被人遗弃了,它们尽管仍然坐落在原来的地方,但却多已坍塌干涸;少数虽然依旧有水,水面上往往浮着尘灰也浮着蚊蚋,就象一位患了白内障、眼珠蒙着一层阴翳的老人般忧郁的望着天空,无奈而凄凉的陪伴着它曾经养育过、滋润过的村落……
而河流呢,那些曾经就是在最为缺水的隆冬时节也没有枯涸过的河流,那些曾经给我们的童年带来过清爽也带来过欢乐的河流,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曾在2010年的冬末春初时节专程探望过扒鱼河,这条曲曲折折流经我出生的村落的河流。那天天色很晚,苍冥的暮色中,儿时的浩淼水波、哗哗涛声早已不复存在,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滩巴掌大的银亮的河水,而这可怜的一点河水,还是村人们修了拦坝积蓄起来的;河水的四周是黑乎乎的更大面积的水藻,几只野鸭凄凉的呷呷叫着,在水中凫游觅食戏逐。它们并不能预测到这点可怜的河水什么时候就会干涸,而当河水彻底干涸的时候,也就是它们失去家园,无奈迁移他乡的时候……
扒鱼河的凄凉现状,正是邓州这片沃土上许多河流乃至渠坝命运的缩影。在夏秋之交的丰水时节,这些河流、渠坝也曾浊浪滔滔的雄壮过,也曾千军万马的奔腾过;然而一当降雨过后不过三天五天,河流、渠坝里的蓄水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类对于地下水无休无止的开采抽汲,造成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地面土壤无法涵水,这样的恶果也只有人类自己来承受了。也许,在将来的一天,那溶溶脉脉的河流,那碧波翻涌的渠坝,终将只会在我们的梦中闪现?而那一辈子只能洗三次澡的人生悲剧,也终将不可避免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